485路公交车行驶到龙和路口时,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弯。此后,一路向南,平稳宽阔的南苑路已被一条狭窄、崎岖的双车道取代。尘土飞扬的路边,大大小小的餐馆、澡堂和各类民房伫立两侧,满载着红砖等建筑材料的蓝色农用卡车不时驶过。
“寿宝庄到了!”汽车骤然停下,售票员大声报站。虽然没有高楼大厦,但这里绝非某条县级公路的延伸,它在北京市五环以内,距天安门广场不过20公里的路程,属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
2010年4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在这里举行“村庄封闭式管理模式推广会”。一项由出入证制度、流动人口管理员和铁门、围墙组成的“村庄封闭管理模式”,随即开始在这里实施。
争议随之而来:“村庄不是看守所”、“封闭式管理无异于有罪推定”……对于“封村”政策,
大兴官方的解释为,社会治安治理的需要。而事实上,这些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村落在实行封闭式管理之时,亦流露出对城市“社区化 ”管理的无限向往。
封村
5月6日,正午,大兴区西红门镇老三余村实行“封村”的第10天。
虽然门口有一道铁门和一道电子伸缩门“把关”,但门口行人出入如常,此前外界猜测的“挨个检查出入证再放行”的场景并未出现。铁门上挂着的一块蓝色牌子,还体现着“封村政策”的余温:“温馨提示:开门时间早6点,关门时间晚23点。”
显然,这只是“封村”政策的一小部分,类似于正门这样的关卡,在老三余村还有14个。原先四通八达的胡同口,如今都统一装上了铁门。晚上11点之后,正门和西北角的大门有人值守,只有持出入证方可出入。
此外,由镇里投入27万元购置的监控系统将在5月上旬安装完毕,届时,摄像头将与西红门派出所联网监控,范围覆盖老三余村的主要地点。
村口的巡逻队员表示,出入证要查,但是一般只是抽查,对于村里那些熟悉的脸孔,“查一次就行了,老查没有意义”。不过,若是在23点到早6点之间回村子,则必须出示出入证。
负责出入证办理的“综治工作中心”就在村口,该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一张空白的“出入证”——一张蓝色的纸质卡片,上面除了填写姓名、性别、民族等,还需注明原籍地址和现住地址以及在京职业、身份证号码、电话等信息。
工作人员称,村里的租客持房东的身份证以及本人的暂住证和身份证便可以办理出入证。
与老三余村一街之隔的寿宝庄村口,大铁门上的标语已由此前的“实施村庄封闭管理,创建生活良好秩序”,更换为更为人性化的“祝全体村民五一佳节快乐”。也许是提前两天“封村”的缘故,这里整体气氛比老三余村更为严肃:伸缩门已被拉上了三分之一,车辆进出必须减速接受检查,两名身着蓝色制服的治安员站在路口,不时对进出的村民进行盘问。
相比邻村,寿宝庄在硬件设施上也毫不逊色。村主干道上已经安装了16个摄像头,此后还将安装15个。其中两个制高点的摄像头,高13米,最大覆盖范围为700米。
来自大兴公安局官方网站的信息这样阐释“封村”部署:今年3月以来,西红门镇金星地区作为试点开始开展“封村、建站、上人防、上技防”四步走措施,随后,该地区16个村庄全部实施封闭式管理。
按照封闭式的管理模式,警方在每个村庄建立村庄综治中心,并联合政府部门为这些村落建围墙、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对村内的人员和车辆实行持证出入的措施,将原本开放的
自然村经过人为科学合理改造,上升为封闭式的社区管理模式。
“以前是一来大事,就封村。”一名住寿宝北部的外地租客说:在此前的奥运会和新中国成立60年大庆时,村子也曾短暂封闭式管理,只不过铁门、摄像头等设施没有修起来,这一次是把“封村”“常态化”了。
流管
“封村”“常态化”的老三余村和寿保庄,由于公交车站名叫“寿宝”,在此居住的外地人往往无法区分这两个紧挨着的村落,于是将这里笼统称为寿宝。
2003年,临近寿宝的北京南五环破土动工,途经于此的公交路线开始逐渐增至5条,便利的交通和低廉的生活成本,开始吸引流动人口的聚集。由此,一个新名词诞生了:“倒挂村”——以老三余村为例,本地村民仅660人,外地人口则多达6000多人,“倒挂”达10倍。
聚居于此的那些被命名为“流动人口”的群体,成为相关部门的管治重点。由此,新的“封村政策”实施后,村里的治安人员被越来越多地称为“流管员”,即负责流动人口管理的工作人员。
和北京周边所有的城乡接合部一样,老三余村和寿宝能聚集起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非一日之功。
最先涌来的是北京南城拆迁所带来的拆迁户。此后几年,随着北京城市规划不断向南拓展,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也向南部转移。一些村民开始在自己的耕地上建起厂房出租,而在村子北部,一些从事服装加工的小工厂已初具规模,制造业带来的外地打工者,成为了这里的第二批租户。
2006年,新北京南站启动建设,北京南站附近由大量访民聚居而成的东庄“上访村”开始衰败,大量访民开始向南迁徙。虽偏远但交通便利、生活成本更低的寿宝,成为继东庄之后的新“上访村”。访民,成为继拆迁户、打工者之后的第三批租户。
人潮拥挤带给村民优厚的房租收入的同时,也给相关部门带来沉重的“维稳”压力。据知情人士透露,寿宝及周边村落的名字,频繁出现在上访者接受询问登记之时,该地区负责流动人口管理的工作人员曾遭上级部门点名批评。
2010年春节期间,一些访民在寿宝附近租住的房间里,自发组织起了一场“访民春节晚会”,这一举动亦让村里的管理部门感到了压力。
社区化
“封闭管理的思路来自于2008年奥运会期间,村里曾实行了类似封闭管理的措施,2009年国庆庆典期间,村里就开始建站了。”据老三余村村支部书记王长祥此前介绍,现在的封闭管理措施是“形势所迫”——2005、2006年以来,随着周边区域的改造和拆迁,老三余村的流动人口激增,现有的基础设施已日益不能承载,生活条件以及治安环境也有所下降。
无疑,治安压力,成为此次封村管理官方给出的主要解读。而此前,大兴公安分局曾从2006年开始,在金星派出所辖区的大生庄村,率先探索“社区式管理模式”,在这之后,该村实现了“零发案”。
于是,2010年3月中旬开始,大兴分局将试点扩大到了金星派出所辖区的寿宝、老三余村等16个村,“下一步将在大兴全区城乡接合部的102个村全面实施”。
此外,部分媒体在探访寿宝和老三余村之后认为,这些城乡接合部的村落产生的“城市化冲动”,亦是可能的一种解读。与之相吻合的是:在4月29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封村”的说法被悄然改为“村庄社区化”。
大兴公安分局局长陈德宝表示,如果在城区买房,不是封闭的小区就是不好卖,“因为不安全。”现在这16个村庄的村民,实际上享受的是城里社区的服务模式。
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认为。“为什么城市居民小区可以如此围墙式管理,正在迈向城市化的自然村就不能照此办理呢?”北大法学院教授沈岿认为,“‘围墙新政’或可在治安方面有一点点获益,却在改善环境和阻止‘私搭乱建’方面难见多大的收益。”
“而政府付出大量的资金投入,外来人口的自由受到一定限制,村里商铺经营性收入或村民租金收入减少等,这都是封村管理的成本。”
沈岿认为,此次大兴“封村”的举措,亦是长期重管制而轻服务的惯性使然,再次“深陷‘要安全,必须管’的思维泥潭”。“殊不知,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社区环境改善、人民安居乐业,同样可以实现安全、秩序与自由之目标。”
面对舆论热议,大兴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认为,对外宣传中,用词不当引发“误读”。“但是真理本身是在辩论中形成的。”大兴区政法委副书记董涛亦表示,在下一步的推广中,会充分尊重村民的意见,加强沟通和协调,针对社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考量。
但是,对于蜗居在老三余村的上访者们,“封村”政策的影响还远未结束。“住一天算一天吧。”冷洪江说,“我们随时准备被轰走,这边不能住了,那就往南,再往南……”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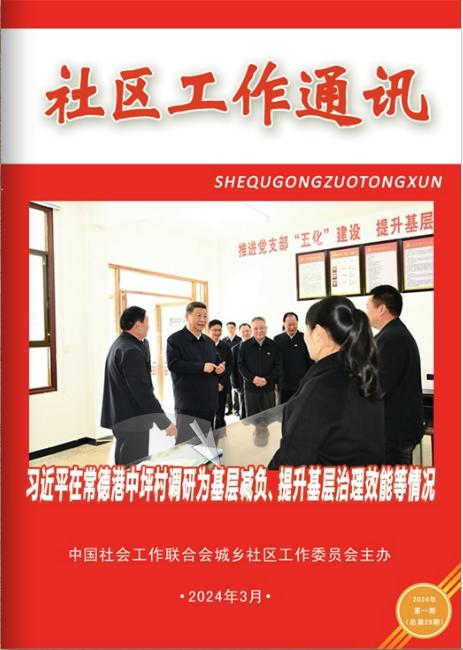
 微信扫码,关注中国社区工作网
微信扫码,关注中国社区工作网